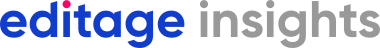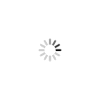- 人物访谈
- 热门
做研究最困难的事情是找到能做的好问题

Tim Hunt 博士以他的细胞周期调控(cell cycle regulation)研究工作以及他与 Lee Hartwell 博士、Paul Nurse 博士一同赢得 2001 年度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而著名。Hunt博士发现细胞周期蛋白,这种蛋白是细胞有丝分裂和其他细胞周期转换的关键。在此之前,Hunt 博士的研究重点是在红血细胞中血红蛋白合成的控制。在经历了漫长且成功的学术生涯,最终他在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Imperial Cancer Research Fund,ICRF,现为英国癌症研究中心)被任命为首席科学家,Hunt 博士目前已经退休。
在上一辑的访谈中,我请 Hunt 博士分享他赢得诺贝尔奖的经验。在这一辑的内容中,我们谈到了他的研究,让他分享在科研生涯早期如何发展对生物学的兴趣。据 Hunt 博士表示,研究人员要成功,必须要有能力找出人们也会有兴趣的“好”研究问题。时程也同样重要,研究人员不能花过多或过少的时间在自己的工作上。Hunt 博士还建议研究人员完完全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即使有时候代表他们要做自己最严厉的批评者。
Hunt博士,能谈谈你的工作吗?是什么激发了你对生物学的兴趣,特别是细胞周期控制领域?
我想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一直想当一名科学家,但生物学完全是偶然!在 11 岁还是 12 岁的时候吧,我在学校的生物考试成绩很好,大概在全校排名第 13 或 14,那是我开始意识到我自己擅长生物学,但我并不是特别喜欢或享受它。我的意思是,我真的很想成为一名物理学家或工程师,因为我喜欢摆弄旧收音机、组装东西什么的,但我对那些其实不太擅长。所以,发现自己擅长生物学的事开辟了我职业生涯,之后只是通过一连串各式各样考试而已。
我认为另一个激励因素是有好的老师。我有一个很好的化学老师,在我六年级时,他把化学教得很简单。同时,在 50 年代末期,大多数学习生物和/或化学的人都会成为生物化学。我还有两个同学选择了生物化学,最后成为生物化学家,对我们来说,生物化学在当时很明显是每个人都想参与的“热点”,我的意思是,我们大概感觉到我们现在所说的“分子生物学”就要崛起了。
然后我和这两个同学去了英国剑桥,我们很喜欢那里!例如,有个生理学课程,我们要进行许多细胞实验,用来补充我的无脊椎动物学课程,比较生物如何处理他们遇到的各种挑战。拿人类生理学跟昆虫生理学或蜗牛生理学比较非常有趣!那堂课的老师使用一个很强的哲学方式。(事实上,这堂课的其中一个老师也教过 Jonathan Miller。顺便说一句,我有一次遇到 Miller 还聊了起来。Miller 还模仿了我们的一个老师,那个老师说话有一个特别的声音。真是美好的时光啊!)
在我们进行第一次动物学商谈时,被问到大学后要做什么,我们三个没有答案,只是害羞地说:「哦,老师,我们愿意做研究。」但是我们当时真的不知道研究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那挺浪漫的。有趣的是,我们并不担心研究是否真的有职业生涯可言,我想我们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而最后也证明是对的,这主要是相信,没有别的。这很有趣,因为今天研究人员更担心是否能有科研生涯,而那个时候,研究是种野心,今天则不止如此。
你是怎么开始细胞周期研究的?
我想,我科研生涯是一连串幸运的突破。
生物化学对我和同时代的人来说是个伟大的选择,因为这个领域还有许多尚未发生的发现,而且看起来很有趣,所以我们就加入了。在我成为细胞周期研究人员之前,在这个领域度过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我当时不会想到自己会踏入细胞周期研究这么专门的领域。在刚开始做研究的那几年,我甚至不知道细胞周期是什么!
我的无知一直持续到我开始做海胆卵的工作时,我才意识到它们实际上是分开的。大约在同一时间,我参加了由伯克利教授 John Gerhart 组织的研讨会,他谈到了 “MPF”或细胞成熟促进因子(Maturation Promoting Factor)这个神奇的东西,MPF 出现在吞噬细胞响应孕酮熟成时。Gerhart 描述的方式很清楚地显示这是细胞周期的关键调节因子,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它是什么。MPF很难净化,但是我仍然想试试看,虽然在当时我从未净化过什么,我的海胆研究和 Gerhart 的讲座激发了我的兴趣,我开始思考细胞分裂。
某个夏天,我在伍兹霍尔海洋学研究所(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WHOI),我们开始想海胆是否有 MPF。我们知道海星有 MPF,那为什么海胆没有?我们试图找出海胆中的 MPF 的研究没有成功,这在技术上太具挑战性。那时我在研究蛋白质合成的控制,所以一开始的研究重点不同,细胞周期研究纯属偶然地引起我的注意。
在研究细胞周期之前,你曾从事血红蛋白合成的工作,能谈谈这部分的研究吗?
有趣的是,血红蛋白合成的工作也是偶然展开的。在我在剑桥的研究生期间,我参加了由 Vernon Ingram 主讲的血红蛋白演讲,这个演讲深深的引发我的兴趣,最后让我研究血红素如何控制血红蛋白合成,这实际上也是 Ingram 研究的领域之一。我也很幸运,因为我的导师 Asher Korner 鼓励所有的学生找到自己的研究问题,并且让他们做自己喜欢的题目,唯一的要求是研究必须在我们的实验室进行。幸运的是,我的实验搭档 Louis Reichardt 在他的本科项目中,他已经学会如何制作兔网织红细胞,这是我做血红蛋白合成实验的先决条件。
后来,我跟一位同学 Tony Hunter 开始研究当核糖体没有足够的血红素时是否形成队列的问题。Ingram 提出核糖体会形成队列。理论上来说,蛋白质会创建一种装血红素的口袋,但如果血红素不足或缺失,它们会等到直到口袋装满后再继续。我们想找出核糖体是如何知道口袋满了。尽管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激进,我们发现这个理论本身是错的,核糖体并没有形成队列。我们确实考虑了我们的方法概率不够敏感,所以无法检测到队列,所以我们思考故意造成队列的方式。最后,我们证明了,如果我们研究预期找到队列,那么我们只会看到这样的结果。我们的方法相当粗糙,而今天的技术能更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但不论如何,我们反驳队列的假设是成功的。
后来在我的科研生涯中,我有了另一个幸运的突破:有一天,我从很长的中午休息后回到实验室,发现我忘了关离心机,这次的疏忽导致了α链多核糖体组成比β链小的发现,这也是我们第一篇《自然》论文。我必须说,这个例子中,即使我们得到了有趣的发现,但我们的解释是错误的,因为我没有执行基本控制实验,这部分后来被 Harvey Lodish 纠正了。
通过我的经验,我了解到只有在遭遇挫折或突如其来的意外时,你才能有所发现。在实验中犯点小错是好的,因为你有机会找到惊人的发现。如果你坚持一条很窄的路,那么你很可能只是做些其他人已经知道的事,而研究的目的是尝试和发现一些新的、没有人知道的东西。但在我做血红蛋白合成的研究过程中,我还了解到,生物化学就是把最细微的技术细节做对,因为如果你没有做对的话,甚至无法开始。
这真的很有趣,Hunt 博士,你看待自己职涯是一系列幸运的突破还有你一路上如何运用学习到的东西。我想每一位成功者都经历同样的过程:把一些事情做对,犯一些错误,从中学习,并即兴发挥。但是当你说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做新的东西,这就跟选择研究问题有关了,在寻找合适的问题时,研究人员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我同意,选择研究问题可能很难,而研究人员没法总是靠运气。多年来我了解到研究中最难的部分是找到一个好的问题。要找到(a)有趣的问题、(b)重要的问题、(c)人们会有兴趣知道答案的问题和(d)实际上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真的很难。研究人员还必须注意时程,我们不是在说一个可以一夜之间解决的小事,也不是说这个东西会永远继续下去,比你的生命还长。原则上,你希望有大一点的问题,可以分解成更小的问题,并在 3 至 5 年的基金申请周期内解决这些小问题。例如,我在 1968 年开始全职研究血红素的问题,然后在 1975 年完成,前后做了 7 年左右的研究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是有解决方案的。
我还记得,当我们开始的时候,必须做很多的背景工作,了解我们将如何进行,我想这点是共通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会一直围绕着主要问题,研究控制让我们对其他相关的机制有很多新的见解。一路上,我还发现,当你的结果会挑战已经建立或被大家接受的研究,你会从许多人那边遭遇更艰难的情况,包括期刊审稿人。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完全确信你的结果,即使这表示你要做自己最严厉的批评者,但总比让别人质疑你或者攻击你的工作来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