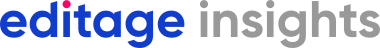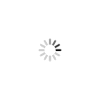读博有感:名利、学问与做人

读博几年,当然早就有感想。这几年写东西又转到私下,而且跟学业和专业有关的占了很大部分。什么时候又愿意重新在自己的抽屉和笔记本之外写东西,我并不清楚。前几年写了点博客,有的文章被人喜欢,也纯粹因为这些就交到些朋友,我深感幸运。另一方面,有时候文字稍微有点儿人看,高兴之余也会不好意思,我的脸皮本来挺薄,也自知人格还没有成熟到一个在公共空间里经常走动的时候。现在也许依然不是时候,不过不写又怎么知道呢?那就写吧,依然从这几年的经历而来的感想开始。
1)名利
很久以前记得看到丘成桐的演讲,说做学问最难的是什么,他说是顶住名利的诱惑。这样的话听着当然一点儿都不新鲜,我一个小孩子当时也觉得很隔靴搔痒:做学问的,包括自己,最初很少有冲着名利去的,真要有名利的困扰也是像他那样拿了菲尔兹奖的人才有的幸福的烦恼。这几年读了点博,才发现远远不是要到了什么菲尔兹奖的程度才算名利,名利的诱惑充满着哪怕起步的学业生活的点点滴滴:选什么课题,找什么老师,去什么学校,写什么文章,露什么脸,甚至在平常吃饭聊天和随便写写的文字之中。读到博士,一般都会在人生中有一些世俗意义上看得见摸得着的些许“成功”的标签,别人会夸你的脑瓜、知识,分数好或者学校好的还会让你分享经验,写文章做客什么的,被别人夸,自己身上也有点好看的标签和小聪明,也就难免得意。只有自己上了点儿道,多了点硬功夫,才逐渐知道世界之大,哪怕一个学科的小领域的招式武艺、前人的积累、未决的问题都深不见底。这种感觉,稍微入行的人都很清楚(我看到很多最好的教授学者就更清楚了)。学术这东西,越往上走越要付出多的多的努力。若还要敢做点和前人稍微不一样,甚至有所突破的东西,智能、体力(是的,学问要体力!)、眼光、时间、训练、导师、还有运气等等可能一样都不能少;知难而上?可能少了几样”成功的要素”?不做也不知道。亦或者差不多就得了,找相对不那么艰难的课题,或者安然地在既有的小圈子呆好了便也不易,更何况到了后头还要考虑养家糊口的问题。
不过之前我以为,上面的各种要素全了,迟早就能做出好学问,而且好的学问名气会大,引用率会高,会拿头衔会得奖。这几年读书,看论文,见人,逐渐发现不是这样。有名气大的,徒有虚名;有的默默无闻,一些人甚至都很难找得到他们的名字或网页,但功夫了得,定力更深,对待名利有嗤之以鼻也有风轻云淡的。这几年博士经历开始逐渐训练我如何抛开标签辨别——这样的辨别需要有缜密的知识、过硬的技术、也要有学科内外全局的眼光,即便这样也还要告诉自己经常会看错——开始能辨别,便要面临自己如何选择。在极少的情况下,天时地利人和,会有几个一帆风顺者,但做好学问,更有可能的是难上加难,不一定成,成了别人也不一定认,认了翻过一座山头又是更难更高的另一座——知道这些了以后,面对每一步的小名小利,如何选择?前几天又读到人类学家项飚说的“悬浮”:悬浮在标签、头衔、出身、指标、圈子之中,自我安慰,自己给自己圆合理性让自己舒服——作为做学问的人,有没有勇气让自己不舒服,有没有冷静在别人的夸赞、漂亮的简历、名校名师、头衔奖励,或者反过来,在这些一样也没有的时候,都有清醒的自知之明。总而言之,“慎独”不易!
2)“学问”与“学术”
“学问”不完全等于“学术”。今天的学术是一类职业,需要专门的训练、有专门的规则、和在这个训练和规则下的人和人群。博士训练有很大一部分也是职场训练,跟其他行业中,人走入社会要找个工作,进入个行当一样。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人的好处和人的问题,跟其他职业也不无不同。一位名校头衔教授可能真的是学问做的好,也有可能仅仅是做“学术”这一门职业的娇娇者。同样,所谓的学术圈也会跟其他有人的圈一样会有体制的问题、成果和上升的压力、投机取巧的空间、私德败坏的学者。每个职业中都会有好有坏。不要混淆在职业之内和之外追求的价值,它们可以有很大的重合,也可以没有。在今天,做好的“学问”多半需要很多的专业化的训练,但专业化的训练可以用来找工作,也可以用来通向自己真正在乎的广阔的个人世界。
我本科的一位古希腊文学的老师,在我大一最困难的时候帮我度过难关。她是美国名校最好的古希腊学者门下毕业。文章写的好,演讲、教学激情澎湃,我今天碰巧翻到之前她在耶鲁任教时学生们给她写的评语,很多学生直言(甚至用大写)说她是他们在耶鲁遇到的最好的文学老师。不过她辗转十几年,最后没有拿到任何地方的终生教职。今天我已经不知道她在哪,网络空间里除了她博士论文的题目和几篇文章之外也已经找不到她的蛛丝马迹。荷马、索福克勒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已在她的血液中成为她的生命力,我也见到这样的生命力如何感召在她身边的那么多人。在今天的人文学科体制里,她的“职业学术“几乎肯定已经失败。但是”学问“呢?也许只留给了自己和能接触到她的身边人。留给我的问题:我当然在具体的专业选择上最终和她有点距离,但是我自觉今后,不管研究写作还是教课,能达到她在古希腊文学里达到的那样的水准,便已要非常庆幸。如此一般追求”学问“,学术也依然可能会失败。面对职业上的成与不成,能不能心里依然泰然不变,克服更多现实的困难,把”学问“做下去?
3)学问与做人
今天,不完全与学问相同的“学院学术”与做人可以完全没什么关系。不过“学问”本身呢(如果还可以在任何意义上谈论学问”本身“)?职业化的学者诞生之前,学问与做人多少是分不开的。而在一些古典学问的理想之中,最高的学问就是做人。我进C大读博,学的是神经科学,这几年,得益于周围的师友和学校本身的氛围和设置,最大的收获之一却在社会学科(人类学、历史、宗教、社会学等等)。当年入神经科学的一个基本动机其实跟我之前的人文底色一脉相承:要问的是人是什么。这几年学到的,却是人的局限和对这些局限的无知:被自己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局限而浑然不觉,更不用说超越的可能。激素水平、基因、早年经历、社会环境、偏见的习得、意见的传染、各种社会和文化的标签造成的“悬浮”、更不用说小到亲人朋友大到社会国家对个人的塑造和影响——很多学者很好的工作便是在梳理和明晰,我们带着自己生物性的躯体在社会空间里游走,何以完全地不知道随时随地伴随自己的无知和无意识,还大多数时候编织出一个自己”完全知道“的梦境(包括这些工作的研究者本身)。以前说人之为人是因为人有自己的”能动性“,而现代自然与社会科学提供的多是各种各样的”被动性“, 或者,套用哲学家Nussbaum有名的话讲,个体——不论是凡夫走卒还是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面对自我、环境和他人之时,从生理条件到道德选择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脆弱与局限。
不过,学理上的些许疏通,影不影响书本外的为人?Nussbaum自己说,她一本接一本的写书教导人的脆弱、友情、爱,却连自己的妈妈病危之时,她还是在开会途中,在飞机上写作。”成功“学者的生活已经让她不想也不愿停下。
我没有答案,我也知道任何可能答案的困难(也许我其实也还是不知道)。不过回到我这几年的经历本身,聪明的头脑、渊博的学识、艰涩的理论、流畅的动手能力、机敏的反应和洞察的直觉、个性和老练的文字和口才我这几年见得不少,不管是读书读到,讲座听到,还是身边就有——在我现在的大学,接触到这些也并不新鲜。但能突破不管是自己的局限还是体制的框架,拥有真正的”个人性“才是世所罕见——这种个体性和我们小时候说的”个性“完全不是一码事,反倒或许和我们平时泛泛而论的”人性“不一而同。许多所谓的个性其实是少年走入成人世界之前,没经过什么考验的浪花一现(当然也有极少的例外,比如诗人兰波,早逝的邹容或者伽罗瓦)。而小聪明能成大人格,却万里出一,且可遇不可求耳。
我也知道,能说这些,并不代表我就能克服名利、做好学问、或是做好人,仅仅是要越来越强烈地警策自己而已。从前看自己小时候的文字会笑,顺便安慰和小时候相比自己确实是有了些成长;而这几年开始经历成人世界的束缚,回望少年时的锐气倒会有留恋和惭愧。年岁的增长并不是意味着进步。相反,在年轻的横冲直撞之后,只能如履薄冰又毫不妥协,原初的生命力才有壮大的可能。更要放开手脚,也更要小心翼翼。
【本文转载自胡茂从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表的科学网博客(原文在此),意得辑专家视点经授权进行转载。】